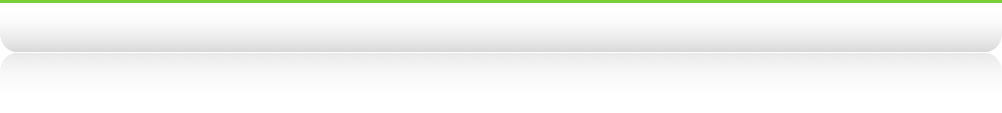公司地址:北京蓝狮在线农产品有限公司
电话:18836426859
传真:400-226-4288
邮箱:7535077@168.com
集团网址:http://www.iyeclub.com/
首页:三牛娱乐:首页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热,可以说从20世纪整个80年代持续到90年代前期,虽然成果很多,但是歧异也不少,计算结果自然也是多种。本文之所以重提这件旧课题,并不是希望重新引发对其的探讨,而是因为近来不断看到引用在引用“剪刀差”来说明农民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贡献时,往往忽略了不同概念和计算方法的差异,数字大的不合情理,从而误导读者。
溯本探源,“剪刀差”概念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剪刀差”最初源于“超额税”。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1923年上半年,政府的工业和商业部门又再次提高工业品价格,使本来已被政府强制压低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又大大降低。到1923年10月,同1913年相比,农民需要相当于原来2.8倍的农产品才能换到等量的工业品。苏联政府的这一行为先是引起农民的不满,农民以不买或尽可能少买工业品来抵制,于是导致工业品市场萧条,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结果又引起工人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九月中央全会。会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第一次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并且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剪刀差委员会,专门从事研究和调整剪刀差的工作。从此,‘剪刀差’这一名词便流传开来。
苏联的“剪刀差”概念在30年代被介绍到我国。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工农生产在战争中遭受的破坏程度不一样,恢复的速度不一样,以及恢复发展工业所需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使得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几年间扩大了很多,1950年工农产品比价与抗日战争前的1930-1936年相比,扩大了34.4%,农民在交换中吃亏很多。因此不少人就采用“剪刀差”这个词来形容工农产品比价扩大的现状,但是此时中国使用的“剪刀差”已经与当年苏联的“剪刀差”概念有所不同了,它不是指那种政府依靠人为扩大工农产品比价来积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表现,而是指工农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状态。例如1951年4月第二次全国物价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就是出自上述概念。以后的学者也多是从这个概念来研究“剪刀差”问题。
可以看出,“剪刀差”概念自被引进我国以后,已经针对中国的国情,被发展和广义化了……正如张西营等概括的那样:“‘剪刀差’是理论界对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的形象概括。从一定意义上讲,工农产品的比价关系的状态、变化趋势,也就是‘剪刀差’的状态和变化趋势。工农产品价格及其比较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是客观事实,用某种标准去衡量这种比价的合理性也就是研究‘剪刀差’的有无、大小。”[1]
剪刀差问题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过两次热潮,一是发生于50年代,针对旧中国遗留的剪刀差和如何缩小它展开的,以1956年在《十大关系》中提出缩小剪刀差、不学苏联后开展大规模研究为高潮。当时主要是研究比价问题,即现在所说的“比价剪刀差”。到1959年,随着工农产品比价缩小到抗战前的水平,一般都认为剪刀差问题解决了,中国已经不存在剪刀差了。第二次研究热潮发生于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1978年以后,鉴于工农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工农产品交换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用比价剪刀差理论显然不能解释。为配合改革,人们开始从价值的角度去研究剪刀差问题,即现在所说的“比值剪刀差”。由于计算和比较价值是件复杂困难的事,特别是在认为价格不能准确表示价值的条件下,因此关于比值剪刀差的研究引起不少人的兴趣,采用了多种计算方法,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
较早研究剪刀差问题的黄达认为:实际资料告诉我们,要想在剪刀差的变动中,也即在工业品价格指数和农产品价格指数的对比变动中找出“等价交换”的点是不可能的。“剪刀差和劳动价值论中的等价交换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也还是远未搞清的问题。”[2]因此,黄达只能在如下两个理论前提下:(1)“在资本主义世界,剪刀差问题的实质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剥削落后的农业,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剥削落后的农村,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剥削落后的农业国,特别是附属国和殖民地。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关系而产生的一个现象。”(2)“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出现始于鸦片战争之后”的理论前提下,考察近代工农产品比价变动情况。黄达得出如下结论:鸦片战争以来,工农产品比价“在不断上下波动的过程中,剪子口张张合合,有时差距很大,但却有一定的界限。就上述的将近百年间看,不论基期选定在何处,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指数,其波动的上限与下限之比很少能突破100%。”但是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世界性的农业危机影响,中国农产品的价格猛跌,剪刀差急速扩大,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受战争的影响,剪刀差继续扩大。1950年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指数,比1930-1936年的平均水平约扩大了34.5%。[3]因此,他对50年代至改革开放以前讨论缩小剪刀差问题时往往以1930-1936年为基期,表示怀疑。但同时也认为并不能拿工业品换取农产品指数的特低点1926年为“基本按价值交换的点”,因而这个点无法确定。
叶善蓬著的《新中国价格简史》叙述剪刀差问题时,即是按照当时的概念,如上所述,以1930-1936年为基期的,这的确也是50年代政府缩小工农产品价格比的参照系和目标。叶叙述,到1957年剪刀差基本缩小到抗战前的水平。对于1958-1978年的剪刀差,则认为表面上看工农产品比价,即剪刀差在缩小,“从1952年到197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72.4%,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0.1%,但同期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1.5%,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24.8%。在剔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之后,从等价交换的角度考察,剪刀差扩大了20%左右。”[4]
李子超等编著的《当代中国价格简史》也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5]到1957年基本缩小到抗战前的水平。对于1958年以后的农产品价格,认为偏离价值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幅度大,这主要是由于压抑农民积极性和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和政策造成的。[6]
严瑞珍等则认为:“剪刀差有两种表现形式,以价格动态表现和以价格偏离价值程度表现。价格动态表现的剪刀差称比价剪刀差,指以一定时间为基期,工业品价格相对愈来愈高,农产品价格相对愈来愈低,在统计图上呈张开的剪刀状。……但是,判断商品交换的价格是否合理,不能仅仅依据商品价格本身如何变化,还要看商品本身所包含价值量的变化。事实上,比值剪刀差才真正反映剪刀差的实质。”[7]
王耕今等使用的概念为:“所谓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是指在交换过程中人为地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一是从价值的角度看,农产品按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而工业品则按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这种由价格反映的价值差距就是剪刀差;二是从交换的角度看,将充分竞争条件下的市场价格视为“等价交换”,而将垄断造成的对市场价格的偏离视为“不等价交换”,这种国家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偏离就是剪刀差。[8]
王忠海则认为:应该还“剪刀差”的本来面目,及“超额税”型剪刀差理论。沿袭斯大林时期的提法,专指政府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或相对提高工业品价格,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的现象。[9]
张西营、邢莹则认为:“剪刀差”是理论界对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的形象概括。从一定意义上讲,工农产品的比价关系的状态、变化趋势,也就是“剪刀差”的状态和变化趋势。工农产品价格及其比较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是客观事实,用某种标准去衡量这种比价的合理性也就是研究“剪刀差”的有无、大小。研究表明,在封建社会,宫廷贵族凭借国家工具,对农民实行掠夺性的价格政策,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剪刀差”;当代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原苏联阵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与我们类似的“剪刀差”;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农产品过剩,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对农产品实行支持价格,形成一种“逆向剪刀差”或“反剪刀差”。可见,理论界虽然对“剪刀差”的有无、方向、大小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总的说来“剪刀差”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清晰的。“剪刀差”的狭义概念固然出自原苏联,却未曾妨碍和局限我们对其进行的深化和运用。既然工农业产品比价是一个客观存在,而该比价又随各种经济关系、经济背景变化而变化,在以往的探索中我们已把不合理的比价关系(交换关系)称为“剪刀差”,现在和未来也同样可以将不合理的比价关系称为“剪刀差”。[10]
韩志荣则认为:“工农商品比价剪刀差计算公式为:工农业商品交换比价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100.另一种计算方法是:把这个公式中的分子作为分母。计算结果,小于100,表示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上涨,为剪刀差缩小,对农民有利,农民的贸易条件改善;大于100,表示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涨超过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上涨,称为剪刀差扩大,对农民不利,农民的贸易条件恶化。”“有的教科书和文章把商品比价剪刀差定义为‘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笔者认为这与上述计算公式不符,与它在历史上的本来面貌不符。因此,我把商品比价剪刀差定义为‘工农业商品比价剪刀差是指工农业商品价格变化趋势的一种经济现象’。从上述大家公认的计算公式看,它是以工农商品价格指数为根据,着眼于价格水平的变化,根本不涉及成本升降以及价值量的变化问题。当然,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的变化可能包括价值量变化以及其他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是需要另外深入研究的问题,但工农商品比价剪刀差本身并不涉及价值量的问题。农民不知道农产品的价值量增加了没有,但农产品交换工业品的数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农民心理是有数的。因此,比价剪刀差具有最直观、最敏感、最为重要的性质,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利益。”为了补充比价剪刀差的不足,他又提出“农民收支比价剪刀差”和“工农收入剪刀差”两个概念。[11]
对于剪刀差差额的计算,显然如前面黄达所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由于建国以来的30年里,工农产品比价在缩小而人们感觉剪刀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因此比价剪刀差理论“失灵”的情况下,比值剪刀差理论则大行其道。人们用来计算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点的办法只能是其价值,而价值中难于计算的,又是工农业产品各自包含的必要社会劳动。于是折合工农业劳动的方法就成为计算剪刀差的关键问题。一个工业劳动力折合的农业劳动力越多,价值剪刀差就越小,反之,价值剪刀差就越大。
最早计算价值剪刀差中工农业劳动比的方法,是按照按劳分配原则,根据工业劳动者与农业劳动者的报酬来折算,认为劳动报酬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劳动差别:我国平均每个工人的月工资60余元,扣除节假日,平均每天2.4元左右,而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的日工分值暂定为0.8元,因此得出三个农民的劳动等于一个工人的劳动。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52年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17.4%,同期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27.3%,剪刀差差额为102.3亿元;1957年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33.6%,同期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38.8%,剪刀差差额为271.6亿元;1977年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34.0%,同期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19.6%,剪刀差差额为690.7亿元。[12]
李炳坤认为上述折算方法不科学:工人的报酬是农民的3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工业品高于价值、农产品低于价值造成的,这种把问题的结果作为研究同一问题的前提,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采用与我国比较的办法来折算: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体上是一个工业劳动力等于一个农业劳动力;苏联自己公布的数字为一个工业劳动力大体等于1.4个农业劳动力;考虑到中国工农业劳动的复杂程度差别比苏联大,可定为一个工业劳动力等于两个农业劳动力。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52年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22.6%,同期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42.0%,剪刀差差额为141.2亿元;1957年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38.8%,同期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53.9%,剪刀差差额为339.9亿元;1977年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14.1%,同期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28.5%,剪刀差差额为934.8亿元。[13]
据杨方勋说:苏联剪刀差的计算方法,是采用先把工业和农业的劳动换算成可比劳动,然后用这种可比劳动所应创造的价值分别与工农业总产值进行比较,其背离的幅度,就是价格剪刀差的大小。可比劳动的换算方法是:由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差别,把工业部门工人的劳动作为标准劳动,等于1,把国营农场工人的劳动打15%的折扣,等于0.85,把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打30%的折扣,等于0.7。这样折算是考虑了农业中一年劳动的天数、劳动力的强弱、劳动的技艺都与工业有差别;这个折算,还参照了苏联工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劳动报酬水平。上述计算的结果,苏联1976年的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17%,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3.5%,剪刀差差额为20.5%。上述计算方法,是以工农业中不存在过剩劳动力为前提的。[14]
严瑞珍则按照工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程度进行折算:“首先,通过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得出工农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差别,再乘以教育费用,计算出工农业劳动力在熟练程度上的折合系数0.7;其次,通过半、辅农业劳动力折合相当于工业的整劳力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求出折合率0.645;综合上述的两个因素,农业劳力折合成工业劳力的折合系数为0.45(=1×0.7×0.645),即一个农民在劳动能力上大体相当于0.45个工人。”根据这一折合系数计算,1982年按全部农产品计算的价格转移总额为740亿元。但是,真正从农业中通过剪刀差转移出农业的只是商品农产品部分,故剪刀差的绝对额应是288亿元。“我们有了1982年作为基期的剪刀差的值,就可以计算其他任何一年(目标年)的剪刀差。办法是:首先找出影响剪刀差变化的诸因子,求出目标年诸因子与1982年相应诸因子的相对数,然后根据这些因子与剪刀差有关指标的比例关系,间接求得目标年的剪刀差。考虑到整个计算要以基期(1982年)的剪刀差的值为参照数,从而把这种方法命名为比值剪刀差动态变化相对基期求值法。”[15]
严瑞珍的计算结果为:“1952年以来,中国剪刀差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以前逐步扩大,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最严重的为1978年,剪刀差比1955年扩大44.65%,达364亿元,相对量上升到25.5%,农民每创造100元产值,通过剪刀差无偿流失25.5元。1978年以来,剪刀差大幅度缩小,1982年比1978年缩小58.97%,1984年、1986年又分别缩小了6.54%和4.55%。但1986年仍然存在剪刀差,达292亿元,而1987年比1986年又稍稍扩大了1.44%。”“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6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剪刀差绝对额。可以说,30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15]
李微也赞同并采用了严瑞珍的这种计算方法。她的计算结果为:1953-1978年间,农民出售农产品少获得的货币收入为2612.6亿元,农民购买工业品多付出的货币为763亿元,即剪刀差的差额为3375.6亿元。[16]与此同时,她与冯海发采用上述方法计算的结果为:“1952—1990年间,我国农业通过”剪刀差“方式为工业化提供了高达8708亿元的资金积累,平均每年223亿元。”[17]
另外,还有按照劳动力生产装备的价值比来折算工农业劳动的。采用这种计算方法的人认为:一个劳动力的生产装备如何对其创造价值的大小有很大影响;劳动创造价值,资金亦应支付报酬。这种方法根据有关资料计算了1980年固定资产装备情况:全国工农业可比劳动力平均固定资产装备额为1788元,其中工业劳动力人均5595元,农业劳动力人均765元,一个工人相当于7.3个农民。[18]根据这种计算方法,反而出现少量的反剪刀差。但是这种计算方法和结果难以令人信服,一是农业固定资产是估计推算的,没有包括土地;二是从经验上也难以相信一个工人相当于7个农民。
韩志荣对上述几种计算方法均不满意,认为没有考虑到工业品的内部交换问题、农产品的商品率问题,以及工农业产品交换中的工业品结构问题等因素,他考虑到上述因素和参考国内外工业利润率,认为“我的初步看法是:我国工农业商品比值剪刀差问题不是很大,即使有也很小”。[18]
进入90年代以后,王耕今等从前述的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前述的几种计算剪刀差的方法不够准确,于是另外采用了两种计算方法。一是从价值角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原理,按照劳动生产率变化来计算剪刀差。其前提是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完全受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并从理论上假定1952年工农产品价格水平是合理的。计算结果为:在1953-1978年的26年间,农产品国家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90%左右;工业品中的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高于其价值44%左右。这种计算方法显然有两个问题:一是农业劳动力和工业劳动力的素质和有效劳动时间上有很大差异(可以表现为劳动力价格),因此其活的劳动也不能只从劳动力数量上和劳动时间上比较,农业劳动主要是简单体力劳动;并且由于农业劳动力过剩严重,平均每个劳动力的有效劳动日很短,这与工业劳动几乎不能相比。第二,国家收购的农产品应该扣除返销于农村的那部分,同样,销往农村的工业品还应该包括生活资料,这部分比重很大,并且价格与城市一样不高。
上述折算,没有扣除农业中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王耕今等的理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实际上是季节性剩余)虽然从理论上说不创造新的价值,但在实际上却要参与分享新创造的价值,否则这部分劳动力就无法实现自身的再生产。因此,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时不应把剩余劳动力剔除出去,这样才能反映包含着经济结构变动和技术变动关系的劳动生产率的线]问题在于,第一,这里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是要计算农产品的价值,用于与工业品比较,因此农产品上凝聚的劳动应是必要劳动或有效劳动,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的数量;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业因体制原因滞留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几乎是不争的事实,把这些人也列入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显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根据计算,1953-1978年的26年里,国家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剥夺农业积累的金额达8019.7亿元,平均每年308.45亿元;同期,通过抬高工业品价格剥夺农业积累的金额达1475.24亿元,平均每年56.74亿元;两项合计达9494.94亿元。[20]
王耕今等的第二种计算方法,是按照国家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偏离程度计算的。其所采用“计划价格”是采用包括超购加价在内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所采用的农副产品“市场价格”,是集市贸易消费品价格指数。根据这种方法,农产品剪刀差主要集中在1960-1978年的19年间,平均差价在58.5%;这19年累计两种农副产品价格差额为1958.71亿元,平均每年103.09亿元;其中粮食一项的差额累计达644.6亿元,平均每年33.93亿元。这种方法虽然可能比前一种按照工农业劳动生产率计算更准确,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后,自由市场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市场价格”,因为在短缺和持币待购的条件下,加上自由市场农副产品供给非常有限,其价格应该高于完全开放的市场价格,这种差额可以与1953年统购统销前的市场价格相比推算出来。但是王耕今等则认为这种方法“不能反映线]
崔晓黎也是采用这种方法。他通过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的国家统购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异,来计算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到底从农民那里获取了多少无偿的资金。他的计算结果为:1959年以前,粮食供销不存在显著的牌市差价:“1960年以后,仅粮食一项通过牌市差价农民实际多贡献的总金额为1318.14亿元,加上农业税(均按可比市价计算下同),总额为3053.7亿元。1960年以前的农业税总金额合计为224.27亿元。这样计算,自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直到1984年,农民实际的无偿贡献总额为3282.97亿元。其它经济作物、畜产品及农副产品的无偿贡献份额,按该项收入通常占农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的概数计算,大约不低于1000亿元,这样全部总额就达到4282.97亿元。”按照上述计算,如果减去农业税,农民通过牌市差价给国家的无偿贡献为2323.14亿元。
温铁军在《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中也引用了上述估算方法:“据估算,1959-1984年国家征购粮食共约1.25亿公斤。统购与市场价格的差额约为2500亿元。”
此外,还有一些没有说明计算方法的数字。如根据张象枢等的计算,1952-1986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加上农业为国家交纳的税收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业新创价值的18.5%。
另根据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和温铁军引用,“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8000亿元。而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25]又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业投入”总课题组估计,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入为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155亿元。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入为175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811亿元。
我赞同张西营、邢莹关于“剪刀差”问题已经由原来的狭义发展为广义的,即对工农业产品比价的研究。但是作为对特定的计划经济历史阶段剪刀差的研究,仍然应该遵循狭义的概念,从剪刀差是政府制定的工农产品价格与市场价格背离的角度,研究农业剩余是怎样转化为工业利润并成为国家工业化积累的。要研究这个问题,由于产品的价值难以判断,而价格的变动则是可查的,因此还得回到最基本的原理,即价值规律:在市场条件下,产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根据这种认识,我认为在研究1949-1978年“剪刀差”情况时,可以假设:在比较充分的市场条件下,即市场配置资源的环境里,即使在某一时期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慢于工业而存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但是这种剪刀差不仅是工业化过程的自然规律,而且是有利于农民向工业转移和加速工业化的,因而最终是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因而对此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不必人为地依据某种理论来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依据这个假设,我们可以姑且认为:在工农产品自由交换的市场条件下,1953年统购统销以前剪刀差即使存在,也是合理的(尽管此后政府努力缩小1953年以前形成的工农产品比价,使其趋于更合理),可以忽略不计。
鉴于计算工农业价值的劳动和劳动率方法很难准确估计工农业产品各自所包含的活的劳动及其价值,因此我采用第二种计算方法,即通过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的国家计划价格与自由市场价格以及国际价格的比较,看剪刀差程度,同时通过扣除国家返销农村的农副产品以及大宗销往农村的工业品数量,来看其差额到底有多大。
②假设统购统销前的1952年集市价格与国家收购价格是一致的。实际上,当时市价确实是围绕国家牌价上下小幅度波动的。
③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贸易物价统计司:《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1952-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如果根据经验和史料来看上述数据,有以下5点需要说明:(1)1960年以前国家收购价格高于集市价格,在1953-1957年,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减少农民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抵触,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吸取苏联教训,主动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但是1958和1959年,则可能是由于实行“一大二公”,集市贸易萧条所致。(2)“三年困难时期”(1961-1963)农产品集市价格与国家收购价格严重背离,是因大饥荒造成的,不应看作常态。(3)这里所用的集市贸易价格指数,在短缺的条件下,由于可供交易的农产品很少,价格应该是高于开放条件下的市场价格。(4)1979年以后,随着国家提高收购价格和农产品供给的增加,集市价格与收购价格之比重新回到1957年以前的状态,很难再说是国家依靠人为定价来获取“剪刀差”收益。(5)由于工业品没有集市贸易价格,无法确定农村工业品的国家和合作社价格与自由市场价格的差异,因而无法判断两种价格的背离情况,但是根据经验和史料,国家提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在1957年以前是有优惠折扣的,1958年以后起码是与城市相同。另外,从农村工业品结构来看,主要是生产资料和普通生活消费品,而在1978年以前,政府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生产资料价格偏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也偏低,农村市价(或黑市价格)高于国家计划供应价格10%应是偏于保守的估计。
这里姑且假设工业品不存在差价。根据上表,由国家通过统购统销获取的农产品计划价格与市价的差额,集中于1960-1978年间,这也与崔晓黎、王耕今(第二种计算)一致。按照上表计算,在这19年间,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共获取牌市价差额3405.7亿元,如果按照农产品收购量中有15%返销于农村来扣除,则国家获取的差额为2894.8亿元。如果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算起,还应再扣除1953-1959年间的负差94.9亿元,则为2800亿元。因此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通过统购统销获取的牌市价差额为2800亿元,约占同期农业国民收入(16523亿元)的17%.而同期农业税则为897.6亿元,占农业国民收入的5.4%。
1、建国以来,在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前提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主观上来说,始终没有像苏联那样故意扩大剪刀差去积累工业化资金,而是试图逐步地缩小剪刀差。正如1957年所说:“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取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
尽管后来事与愿违,但这一点是必须澄清的。2、过去过高估计了剪刀差差额,夸大了国家对农业剩余的索取。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前主要的问题是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生产制度束缚了农民的自主权,压抑了其发展农业的积极性,限制了广大农民向利润高的非农产业转移。换句话说,限制了农民把蛋糕做大,因此国家即使拿走不多,农民仍然很苦。假设如果现在继续不让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和流动,仍然将其束缚于集体生产的农业,即使将全部农业剩余都归农民所有,其出售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持平,农民仍然非常贫困。
3、通过剪刀差转移的无形的农业资金,是通过工业部门的低价原料、职工的低工资(即降低成本)方式,以工业利润形式积累起来,并不是国家直接额外拿走了如此数量的实物。
4、由于夸大了剪刀差差额,就忽视了工业在积累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即使扣除剪刀差的因素,工业本身的发展和积累,仍然是我国工业化的主要途径,大力发展工业和非农产业,加速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才是解决农业落后,增加现在农民的根本途径。
5、夸大剪刀差,还容易导致忽略资本、技术,特别是人力资本的作用,忽略新兴产业应该得到的包括风险和创新收益在内的高额利润。
6、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试图通过人为的办法来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不利于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可以采取减税、扶持农民发展非农产业、减少农业人口以及鼓励农民流动等办法解决。
近日在罕见论坛读到网友转贴的署名白沙洲的农民问题系列文章,经检索发现,该系列来自多维新闻社所推荐并提供在线推销的白氏著书:《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明镜出版社2001年9月发行,ISBN 962-8744-56-89,售价: $19.00)。笔者在粗读了此书部分内容后,一方面对于白氏花费了大量时间与文字来描述中国农民问题的来龙去脉,探究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并呼吁提高其地位,笔者认为这样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笔者不能不指出,白氏书中在数据、史实以及诠释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偏颇乃至失实之处,读后令人深感不安。
笔者刚刚旅行归来,对此书读得比较仔细的只是在多维周刊上连载的第17回:“强盗来了--统购统销”那一篇(附后),发现在这短短的一篇之中,著者对于国家曾经实行的“统购统销”体制,从基本认识、引用的数据直至结论,都是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在此篇中,白氏集中攻击统购统销政策及其对农民的所谓“剪刀差额剥削”。在白氏眼中,共産政権是“强盗”,统购统销是“强盗制度”,广大农民便是被“强抢”的对象;共産政権这个“强盗”正是通过统购统销这个“强盗制度”,得以从农民手中抢走了天文数字般的钱财。白氏认为,揭露这一点“可以帮助那些即使最没有文化的人懂得为什么农民如此赤贫。”
我们来看白氏是如何进行他的推理和得出结论的。他首先举了张爱玲散文《秧歌》中劳动模范金根的例子,来说明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民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了这个垫铺之后,白氏笔锋一转,“就在中国农民处于这样一种生活境况下,共産政権居然还在想方设法在农民身上打主意。”“从1953年开始,统购统销开始实行”。那么,这种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制度呢?白氏借用《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所形容的“强盗制度”一语,然后推出了凌志军写的一堆不伦不类的类比文字并罗列了一堆离题的(比价)剪刀差额数字;白氏认为,这样他就可以证明共産政権通过统购统销这个“强盗制度”从农民身上闷声发了大财,于是,农民便贫困了,共産政権自然便是“强盗”了。
白氏的这种写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在此我们也就不一一计较了--诸如,引用散文和记者报道来写历史的方式是否恰当,财富被“强盗”抢去之后下落如何,著者是否真正搞懂了“剪刀差”这个概念、它与统购统销有什么关系以及是否可以用比价剪刀差数字来说明比值剪刀差(统购统销只产生比值剪刀差)的命题,如此等等。笔者在此想要澄清的,主要是下面的三个问题。
有关国家在1953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和专文阐述。笔者这里想要说明的只是,统购统销政策主要是一个针对市场的政策,它不是一个针对农民的政策,更不是为了在农民身上赚钱。
建国初期(1950年4月~53年11月)的国内市场曾经存在过由国营商业执行的、用挂牌方式公布的国家计划价格(牌价)与由私营商业(包括其他非公营商业)操纵的自由市场的成交价格(市价)这两种价格体系。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便是这两种价格体系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较量的结果。国家在制定牌价时的目的和基本原则是,既要照顾到生产、贩运、消费三个环节各方的利益,又要促进生产和流通、保证在有限在财力物力下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实现;而私营商人在设定市价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牟利。
这种根本性分岐决定了国家在与投机商人和个体农民(农产品销售者)所进行的竞争当中,必须时时盯紧各市场主要商品的产销、流转、供求、价格及商人动态、金融货币等情况,搜集、统计、积累和研究各种有关物价的资料市场动态,频繁地调整粮价,稍有疏忽,就会引起市场波动和供给矛盾,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这对于刚刚建政、工作千头万诸的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件高成本的事情。据徐建青《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从价格机制到统购统销》一文中叙述,1950年4月1日至1953年6月9日,国家曾先后15次由贸易部、商业部、粮食部等部门牵头调整农副产品牌价(含下调10次和上调7次),其中粮价的调整趋势是先降后升。然而,这种调整本身并不能产生价值,除了需要为之徒付高昂的管理成本外,对于国家急需的资本积累、战备与救灾粮食的储备,以及为开始起步的国家工业筹措原材料而言,市价对于牌价的拮抗常常起到了破坏国家计划目标实现的作用。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1959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市场上棉产品以及其他工业品的价格迅速上涨,而同时由于夏秋粮丰收和国家收购不力等因素,市面上粮价反而下跌得厉害,不少粮食产区的市价低于国家牌价。而由于朝战爆发,9月份中财委提出需要大量收购粮食,准备囤积50亿斤。但是事与愿违:一方面,投机商人乘市价低于牌价之机先按市价大量买进粮食,再按牌价卖给国家,从中牟取暴利;另一方面,农民坚决要求国家按牌价收购粮食,这种价格上的两轨制大大增加了国家收购资金的支出,最后使得中财委的囤粮计划化为泡影。
因此,在1953年11月以后,国家对农业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并关闭部分自由市场,这不仅是市场运作本身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建国初期中共中央为打假制伪、整顿当时的市场和财经秩序,以微弱国力建立起计划经济的目标体系,缓和工农业发展不平衡与供求矛盾,集中精力和本钱为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准备条件与环境的一个重大战略抉择。也许,这样的抉择并非唯一的选择,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怎样一个抉择都会有风险、都存在着利弊得失;选择一个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和发展目标、预期收益很可能大于耗费成本的方案,无疑是明智的,选择统购统销制度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也早已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当然,在任何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之中,干部们在执行政策上不可能不出一点偏差,也必然有一部分人是利益获得者而另一部分人是利益失去者,由此分化出赞成的和抵制的两派力量,且有可能伴随或多或少的冲突甚至是暴力事件的发生。这在世界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是常识,而关键要看在变革过程中获益人数与失益人数的大体比例。事实上,直到1960年前,每年国家的统购粮价都高于市价,这使得占农村人口八到九成的广大农民获益(共获益94.9亿元,见后述)。对于这大多数的农民来说,统购统销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在统购统销中,私营粮行的老板、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以及少数从事投机贩卖的个体农民失去了原有利益,成为统购统销的抵抗势力。但这些人所占,不过农村人口的一到二成而已。
如此利国利民的好事到了白氏那里,怎么就成了“强盗制度”了呢?白氏在书中收集到了在某些地区发生的抵制统购统销的冲突个例(注意:与政府冲突的多为从事投机交易的私营商人、个体农民以及地主富农),便以为找到了否定新制度的根据,这是十分可笑的。
此外,对于国家来说,等于是把原来可能装进少数投机者口袋中去的钱,换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同时省去了大量本来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有人要问,这样国家不是钱多了吗?国家把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是转移去了国家建设,还是象白氏形容的“强盗”逻辑那样被坐地分了“赃”,对此,我想读者自有明断。
白氏为了“论证”统购统销是一种“强盗制度”,引用了《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所做的一个十分不伦不类的类比:“ 所谓统购,也即种棉者必须将棉花卖给政府,且必须依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卖给政府。这是在世界各国中极少有的想像。好比一个乡下人走到城里商店中,见一电视,标价是3000元,他于是对售货小姐说:『不行,你只可卖2000元,而且你必须把它卖给我。』人人都知道这是不讲理的行径,决不可能得逞的,搞得不好人家要当他是神经病,甚至去叫警察。但是,城里人到乡下向农民收购棉花,大致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你必须按照我规定的价格把棉花卖给我。”
这个“2000元强买3000元的货”的类比表明了原作者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无知。
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出在1953年至1983年期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中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变动的大致情况。
1)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初期(1953~1959年),国家对于农副产品的收购牌价(每年均)高于自由市场的成交价格即市价:牌价平均指数是116.5,而市价指数只有109.7,前者高出后者6.2%左右。政府这样做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要减少农民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抵触以顺利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吸取苏联教训,主动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正如在1957年所说:“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显然,这个时期的实践与的初衷即让农民得到实惠,是完全一致的。按照比值剪刀差来计算,7年之中国家倒贴给农民的金额是94.9亿元(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2000年)。
回想起白氏对于统购统销的出台曾惊呼“强盗来了”,这真实让人啼笑皆非:天下难道有愿意倒贴本钱来予人实惠的“强盗”吗?
2)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1963年这几年市价和牌价出现了大颠倒,这几年的情况是,自由市场十分活跃,半数以上的余粮在这里成交,因此不应被看做统购统销政策下的常态。
3)1964年起,回到了市价与牌价偏离不大的常态。但是与初期不同的是,直至1978年,牌价始终低于市价,平均低约18%(至1983年低约11%)。牌低于市便形成了正值的剪刀差。因此,如果要说统购统销制度“剥削”农民的话,指的应该是这一段时期。然而1964年距离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1953年已过去了11个年头,有谁能够证明,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正值剪刀差,乃是共産政権的出台统购统销制度伊终便打好的主意呢?
──根据崔晓黎、温铁军、王耕今等、和武力等人独立计算的结果(见后述),在建国后的前30年中,国家借助于牌市差价、通过统购统销农副产品得以转移到工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剪刀差差额资金每年平均72.6~107.7亿元。扣除国家每年的对农投资平均65亿元左右,则年均转移资金7.6~42.7亿元。按全国6亿农民保守估计,等于每个农民每年受国家“剥削”了1.6~7.1元。试问最有文化的白先生,这每年区区数元的“剥削”,就“可以帮助那些即使最没有文化的人懂得为什么农民如此赤贫”的原因了吗?
──实际上,如上面表中列出的,在1964~1983年期间,国家对于农付产品的收购价格比1952年上调幅度平均达到84.4%,而同期对农工业品(农具、化肥、农药等)的零售价格仅上升了2.4%。换句话说,这不是在以农养工,倒是在以工养农了,这其实就是一种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比价剪刀差)、予农民以实惠的实际措施。试想一下,如果在1964~1983年期间也象近十年来这样大幅度地上调农具、化肥和农药零售价格的话,那么,那时农民种田的成本又当上升几何、农民的实际收入又当下降几何?
──正如武力所指出,国家对于农业通过统购统销获得的无形的农业资金,是通过工业部门的低价原料、职工的低工资(即降低成本)方式,以工业利润形式积累了起来,并不是国家直接额外拿走了如此数量的实物,更不是有什么“强盗”在那里坐地分过什么“赃物”。优先发展工业是国家战略,在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再回过头来通过下调对农工业产品的价格来对农业进行补偿。根据《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1952-1983)》中的数据,1972~1976年这5年中对农工业产品的零售价格,确实已略低于1952年的价格水平。
白氏愤愤然道,“就是这样一种强盗般的制度,统购统销的设计师陳雲还在那儿说「价格公道」”。对于白氏的愤然,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事实无情,白氏算是白愤然了。根据上面的数据和分析结果,相信“即使最没有文化的人”也能懂得,统购统销制度下的农副产品价格确实是相当公道的价格。
白著中接下来的部分中一气举出了六组“剪刀差”数字,用来回答“30多年的统购统销,共産政権到底从农民手中弄走的财产值多少钱”的问题。这些剪刀差数字大致从5100亿到8000亿元人民币,每年平均200~300亿元。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数字大都是“比价剪刀差”的数字,即由于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不同,在交换过程中给农民带来的损失金额的估算。比价剪刀差的概念说形象一点,就是以一定时间为基期,如果工业品价格相对愈来愈高,农产品价格相对愈来愈低,那么在统计图上便会呈现出张开的剪刀状,上下刀口的差值就是比价剪刀差。理论界经过多年的讨论,已经认识到用比价剪刀差的概念来计算统购统销政策下的资金积累是不合适的,因为中国的统购统销基本上不出现比价剪刀差,而只出现比值剪刀差。
第一,新中国的比价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1950年工农业品比价与抗日战争前的1930~1936年相比,扩大了34.4%,农民在交易中吃亏很多。在1956年《十大关系》中提出缩小剪刀差、不学苏联的要求,经过人的努力,到1957年比价剪刀差已基本缩小到了抗战前的水平(李子超等:《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叶善蓬:《新中国价格简史》)。因此说,白氏如欲“控诉”什么的话,他理当控诉和旧社会;反过来,白氏如欲“歌颂”什么的话,他理当歌颂和新社会,这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二,应该看到,工农产品的比价剪刀差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黄达认为:要想在剪刀差的变动中,也即在工业品价格指数和农产品价格指数的对比变动中找出“等价交换“的点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剪刀差和劳动价值论中的等价交换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也还是远未搞清的问题(黄达:《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第三,1953年到改革开放前,工农产品的比价实际上一直在缩小,在这个意义上说,统购统销政策是不应出现比价剪刀差的。换句话说,白氏使用比价剪刀差的概念来“控诉”统购统销制度“剥削”了农民,不过是在缘木求鱼。
尽管工农产品的实际比价一直在缩小,但1978年后人们仍感到剪刀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于是比价剪刀差的理论失灵,人们开始从价值比较的角度去研究剪刀差问题,即现在所说的“比值剪刀差”。另一方面,夸大剪刀差额,会在实际中忽视工业在积累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经验证明,即使扣除剪刀差的因素,工业本身的积累仍然是我国工业化的主要途径,大力发展工业和非农产业,加速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才是解决农业落后,增加现在农民的根本途径。
计算和比较价值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因此,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不尽一致的比值剪刀差的测算结果,计有
──反剪刀差(见李炳坤转述):按照劳动力生产装备的价值比来折算工农业劳动,一个工人相当于7.3个农民,据此算出了少量的反剪刀差。
──韩志荣:计及工业品的内部交换、农产品商品率、工农业产品交换中的工业品结构等因素及参考国内外工业利润率的结果,认为“我国工农业商品比值剪刀差问题不是很大,即使有也很小”(《关于工农业商品剪刀差三个重要问题的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1990年第11、12期)。
──崔晓黎:按照国家计划价格与市价的偏离程度计算出,1953~1984年的粮食比值剪刀差加农业税为3282.97亿元,其它作物类则不低于1000亿元;总额4282.97亿元,减去农业税后为2323.14亿元,年均72.60亿元(《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温铁军:类似于崔晓黎,根据1959~1984年国家征购粮食共约1.25亿公斤,估算出统购与市价的差额约2500亿元,年均96.2亿元(《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王耕今等:类似于崔晓黎的方法,计算出1960~1978年间统购统销获得价格差额1958.71亿元,年均103.09亿元;其中粮食差额644.6亿元,年均33.93亿元(《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武力:类似与王耕今等,计算出1953~1978年间国家统购统销获取的差额为2800亿元,年均107.7亿元(《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2000)。
──张象枢等:采用方法不明。计算出1952~1986年的剪刀差额为5823.74亿元,年均166.4亿元(《中国农业巨变与战略抉择》,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
──李炳坤:按1个工业劳动力等于2个农业劳动力估算,1952年剪刀差差额141.2亿元、1957年339.9亿元和1977年934.8亿元(《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李微:按照工人和农民的文化程度等折算出,1952~1990年间剪刀差差额达8708亿元,年均223亿元(《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等等。
从反剪刀差到年均223亿元的种种结果,真是纷纭众说,莫衷一是;其中占主流的是崔晓黎、温铁军、王耕今、和武力等人的数字,显示了在建国后的前20余年中,国家通过牌市差价每年平均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及其他行业的比值剪刀差差额资金在72.6~107.7亿元之间。扣除国家每年的对农投资平均65亿元,则平均每年的转移资金在7.6~42.7亿元之间。按全国6亿农民保守估计,摊到每个农民头上每年的转移资金就是1.6~7.1元,这么点钱(抛开以工补农的补偿优惠不论)又怎么可能成为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呢?
1.1953年11月后国家所实行的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是当时的市场运作本身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中共中央为了打假制伪、整顿当时的市场和财经秩序,缓和工农业发展不平衡与供求矛盾,集中精力为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准备条件与环境的一个重大战略抉择。统购统销体制在当时条件下,于民有利,于国有益,并且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其他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此利国利民的好事,怎么到了白氏的嘴里,竟变成了所谓“强盗制度”了呢?
2.新中国的比价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过人的努力,到1957年这个剪刀差已基本缩小到了抗战前的水平。因此,理应歌颂和新社会,理应控诉和旧社会,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3.新中国的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和外国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的强盗行径,有着天壤之别。
4.比价剪刀差是天然存在的,人为地去消灭它并不太明智。统购统销政策不出现比价剪刀差,白氏使用比价剪刀差的概念来“控诉”统购统销体制对农民的“剥削”,是缘木求鱼。
5.很多人不赞成过去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因为多年来的宣传总是说,统购统销通过压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来从农民手中赚取财富。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在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初期的1953~1959年,国家收购价格比市价高出4.6%~10.6%,形成了负值剪刀差,国家因此每年平均倒贴给农民13.6亿元,每人年均2.7元。
6.在统购统销政策实行的后期(1964~1978年),国家收购价格高于市价8.2%~29%。牌低于市,形成了正值剪刀差。专家的测算表明,综合正负剪刀差,在实行统购统销体制后的20余中,国家通过牌市差价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及其他行业的比值剪刀差差额在扣除了国家对农投入之后,每年摊到每个农民头上仅1.6~7.1元。这点钱,是无论无何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的。
7.本文不是要否定白氏书中的其他章节和全部观点。白氏敢为中国农民鼓与呼的精神值得肯定。然而,限于其人对共産政権的偏见以及对于史实了解的不够认真和深入,其在“强盗来了--统购统销”一篇中的立论是错误的,所采用的数据是不实或不能说明问题的,其强词夺理、东突西厥式的行文是轻浮的。笔者在祝愿白氏卖书卖得好价钱的同时,亦恳望如此文风能成为天下学人著书时之慎戒。
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民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从张爱玲的《秧歌》中的主角、劳动模范金根的生活状况就可以看出。金根虽然生活在江浙地区这样的传统鱼米之乡,家里只有三口人,但吃顿「煮得硬点的饭」、「不要那稀里光当的东西」、要那米一颗颗的数得出来」还得下大决心。尽管如此,但他的生活仍是紧巴巴的。「妻子端上来的仍然是每天吃的那种薄粥,薄得发青;绳子似的野菜切成一段段,在里面漂浮著」。即使这样的饭,五岁的小女儿也总是缠着要吃;吃不上,就去偷看下乡创作电影的城里同志吃,而为此一次次挨打。
临近过年了,金根家的饭是「米汤里连一点米花都看不见!」「饶这么着,我们的米都已经快没有了。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心里就像滚油煎的一样。」在金根这个劳动模范的眼中,如果能够收成「九担谷」即900斤,一家三口能够每天有2斤半米,就是他这个农民最大的愿望。
就在中国农民处于这样一种生活境况下,共産政権居然还在想方设法在农民身上打主意。从1953年开始,统购统销开始实行,这一制度持续使用的时间长达32年,到1985年才结束。其间横跨毛沢東、鄧小平两代中共领导,今天的第三代中共领导人对这一制度仍呈犹抱琵琶半遮羞状。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以棉花为例(统购统销之一种),形象地将这种制度比作强盗制度。「所谓统购,也即种棉者必须将棉花卖给政府,且必须依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卖给政府。这是在世界各国中极少有的想像。好比一个乡下人走到城里商店中,见一电视,标价是3000元,他于是对售货小姐说:『不行,你只可卖2000元,而且你必须把它卖给我。』人人都知道这是不讲理的行径,决不可能得逞的,搞得不好人家要当他是神经病,甚至去叫警察。但是,城里人到乡下向农民收购棉花,大致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你必须按照我规定的价格把棉花卖给我。」
有材料披露说:广东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夜晚偷偷地派人去看粮食仓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见到调运粮食的船只开走后在河边哭泣,有一农户在家中半夜点灯算粮食是否够吃。
就是这样一种强盗般的制度,统购统销的设计师陳雲还在那儿说「价格公道」。1954年9月28日,陳雲在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为这一制度辩护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对于农民都是有利无害的。如果不这样作,农民就会回到旧社会。1954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也大谈《统购统销对农民的好处》,1957年,毛沢東亲自出马,向那些对统购统销存有疑虑的省市委书记说:「我们统购统销,是按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
30多年的统购统销,共産政権到底从农民手中弄走的财产值多少钱,中共官方至今没有给一个正式的说法。下面只是列出一些研究者发现的大体数字,这些数字也可以帮助那些即使最没有文化的人懂得为什么农民如此赤贫。
1。凌志军认为:在50-70年代的三十年间,农产品的低价统购统销、农村工业化的税收政策,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方式,从农村拿走了大约6,00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后来被证实了。
2。据估计,30年来在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藏的农民贡赋达8,000亿元。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主编的一本书认为:据计算,1952-1986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拿走5,823.74亿元,年平均为200-300亿元。
4。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约占这些年农业所创造价值的18.5%。
5。据有关部门测算:1951-1978年,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形式,政府从农民手里拿走了5,100亿元。
6。据雷锡易等人测算,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通过剪刀差方式向工业转移的剩余为6320亿元,加上农业税共达7,264亿元。扣除国家给农业的发展、建设等方面的资金1,730亿元,农业实际向工业净提供资金5,534亿元,平均每年205亿元。
张西营、邢莹:《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黄达:《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黄达:《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1-2,6,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叶善蓬:《新中国价格简史》,178-179页,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
李子超、卢彦:《当代中国价格简史》,26页,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李子超、卢彦:《当代中国价格简史》,78-79页,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
王耕今、张宣三主编:《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88-89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张西营、邢莹:《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韩志荣:《工农三大剪刀差及其现状分析》,《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
李炳坤:《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44-46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李炳坤:《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48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转引自杨方勋:《农产品价格研究》,118-1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
李微:《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302-30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冯海发、李溦:《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韩志荣:《关于工农业商品剪刀差三个重要问题的研究》(下),《价格理论与实践》1990年第12期。
王耕今、张宣三主编:《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113-114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王耕今、张宣三主编:《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75-76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王耕今、张宣三主编:《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88-102页,110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崔晓黎:《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33页。
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175-176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张象枢等:《中国农业巨变与战略抉择》,47页,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
]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177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农业投入总课题组:《农业保护:现状、依据和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